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一):新疆圈地与民族矛盾的崛起
解放报 作者:雨舟尔巴切的故事
2017年8月18日,一位名为尔巴切(音)的中年卡车司机停在矿场卸货时,他老家的公安突然前来寻他。前一天,千里迢迢从他家乡跑来这里找他的老家公安已经收走了他的手机。虽然觉得奇怪,无信仰也从未触犯过法律的尔巴切并不害怕,他只担心警察会追究一些未支付的交通罚款。可尔巴切未曾料到,几个小时后,他将被带回家乡,绑在老虎凳上。当时的恐惧至今是他甩不掉的梦魔。
审问尔巴切的警察问了他一些问题:“你有没有去过清真寺?有没有在哈萨克斯坦祈祷过?为什么要去哈萨克斯坦?你喝不喝酒?手机上为什么有脸书,Instagram,WhatsApp等境外App?”身为哈萨克族的尔巴切答道,自己挺喜欢喝酒的,有时候还会说脏话,有这些App是因为他的很多哈萨克斯坦朋友都用,但反正在国内都用不了,有什么问题吗?
再过几个小时,尔巴切被带到医院做“健康检查”。他被拍照,抽血,录了指纹、声闻,做了虹膜扫描。凌晨两点,“检查”完了,他被戴上手铐,拉去看守所。
看守所里的人很多经历跟尔巴切相似。有一些是因为买了前往土耳其的机票被拘留,有一些是因为去哈萨克斯坦学习或探亲引起了怀疑,又有一些是因为祈祷太频繁或者因为戒了烟惹得麻烦。其他囚友听说尔巴切是因为手机上有WhatsApp被拘留,都说应该很长时间出不去了。
在看守所里,生活比正规再教育营更加难堪。他们每天6点被叫醒,要求带着脚铐在囚室里跑步,脚腕的皮肤经常被脚铐磨破。跑完步,他们会被要求坐在床上不动,如果动了,会引来一顿棍打。因为打的是屁股,受过罚的人第二天很容易坐不稳,再次被木棍伺候。
后来,尔巴切被转移到了正规再教育营。在那里他们白天不允许坐床上,夜里从不关灯,要吃饭必须先热烈唱爱国歌曲,每天看大量汉语政治教育节目。尔巴切发现一些营里的工作人员是他前辈子认识的人,曾经的同学、同事。他们私下提醒了尔巴切,一定要积极表现,不然可能惹来麻烦。已经会汉语的尔巴切算是幸运的,每周的学习、唱歌和写思想报告任务对他来说不算太难,表现好导致他可以少受苦。也部分因为尔巴切会汉语,2018年11月,营里开始招人去工厂工作时,尔巴切因为思想和汉语考试表现不错,成为了被挑选的幸运小数。
聘用尔巴切的工厂建在营里面。厂里有300台缝纫机,新招的囚犯首先被安排做校服,后来技术提高了,再开始做带有南航商标的布餐巾,他们的工作由两位汉族女管理监管。工人们白天工作,晚上回教室唱歌、做思想学习。有一天,厂里来了一些访客,两位管理提醒工人,要跟客人说自己原来是失业的,是自愿来这里学习技能,这是党对自己的照顾。当天的访客是两名记者。
关押了一年多之后,尔巴切有一天突然被放出来。他后来得知,这是因为他妻子已经成功入了哈萨克籍,并开始积极申诉要求把他放出来。也是因此,他才终于脱离了被关押,被强迫劳动的日子。直到尔巴切离开了再教育营,他都没有收到过一分钱工资。
看不到的白色恐怖
自2017年,新疆有高达15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人被关入再教育营。这意味着新疆的约1500万名穆斯林中,有接近10%被“消失”。他们分别被关在看守所、再教育营和监狱里。根据卫星图、政府招标信息以及前囚友和营工作人员所提供的信息,新疆目前建有300多所再教育营。此外,在2017至2020年间,新疆有53.3万人被刑事起诉,为全国人均的六倍;“潜在犯罪人士”被关入再教育营,而这部分已经被判罪的人则被关进正式监狱。同时,哪怕有幸留在营外的新疆少数民族,也生活在一个“室外牢笼中”:他们受到密布监控系统的监视,没有通行证不得出县,隔三岔五有警察上门检查家里是否有任何信教或其他“异常”表现,查出异常随时可能消失到“黑门”(本地人对再教育营的浑称)后。这些实体和隐形的牢笼近年渗透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恐怖,一个民族围剿系统。因此,在最近因新疆一场大火而爆发的解封运动中,虽然火中死的都是维族,上街反抗的维族很少。被白色恐怖笼罩多年的新疆少数民族,都明白上街就意味着将消失到营里。
在信息管控的环境之下,我们在国内很少能接触到任何关于这场在国土上上演的白色恐怖的消息。如果能看到,也通常只有西方帝国主义媒体提供的片面消息。新疆这场愈演愈烈的民族围剿成为了西方最喜欢探讨的中共(以及共产主义)罪状之一。他们以新疆为例,证明“集权”的邪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指控的虚伪,我们当然清晰——在美国,少数民族也被大量拘禁,被剥夺权利,更不用提美国在自己的边境外所行的罪恶。但是同时,这场恐怖的民族打压,并不是一个西方编造的谎言。作为关心全世界无产阶级命运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能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实际上,新疆少数民族的命运,也跟我们所有无产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我们该如何跳出美帝的反共宣传,去理解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的遭遇,去了解这个遭遇与我们自己的关系?
开头的真实故事,来自人类学家达仁·拜乐(Darren Byler)的著作《在营里》(In the Camps)。基于他从2011年至2018年累计在新疆做的研究,拜乐的两本书《在营里》和《恐怖资本主义》(Terror Capitalism)❲1❳记载了新疆的资本侵入过程,它的民族和阶级关系,以及它的庞大民族围剿系统的崛起。这两本仔细记录了新疆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了解新疆现状的线索。根据拜乐以及其他材料所提供的信息,这系列文章将试图打破“集权”的视角,从资本运动的角度来理解新疆的民族矛盾和今天形成的白色恐怖。❲2❳第一篇(此篇)将介绍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侵入新疆、民族矛盾激烈化和“反恐”系统崛起的过程。第二篇将分析在这种新的资本主义运动之下,所形成的民族和阶级关系。第三篇将试图解释新疆民族围剿系统的出现,介绍类似手段在资本主义阶级统治上的历史,以及再教育营系统与如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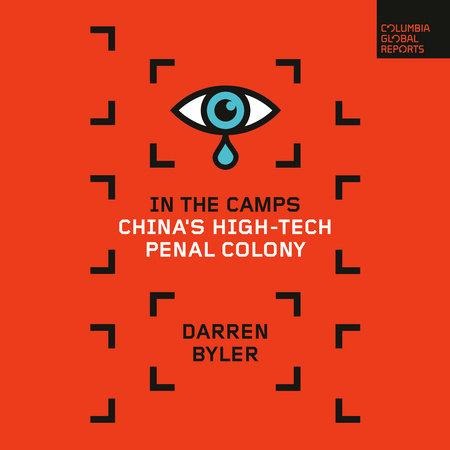

这三篇文章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我们对国家性质的认识:特色政府的最重要特征,不是集权,而是它的资产阶级性质。新疆少数民族如今的遭遇,跟资本、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在拜乐记录的历史和描绘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这场民族围剿背后的资本驱动。
本文将首先介绍新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分析新疆民族矛盾的出现跟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我们将回顾新疆的民族围剿系统——它的全方位监控和再教育营——的逐步建设过程。
重现的民族矛盾
历史上常为多方势力争夺之地的新疆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地方。新疆有12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数最多。3解放时,新疆超过75%的人口为维吾尔族。如今,维族大约占新疆人口的一半。新疆的少数民族有与汉族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在中原(汉与非汉)朝廷断断续续几段对新疆的统治之下,封建皇朝的阶级和民族压迫,埋下了难以一时化解的民族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毛时代建立在民族自治基础上的相对和平的民族关系,是一个不能轻视的成就。而80年代以来民族矛盾的重新激烈化,也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
虽然不能幻想毛时代不存在民族矛盾,但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消除,民族自治以及工人和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无疑提供了更加和平的民族关系的基础。无论不同时期统治新疆的是哪个民族的贵族,解放前的新疆基本社会结构都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极少数人拥有大多数土地、农民深受压迫的封建社会。而解放后,新疆统一为新中国的一部分,是建立在民族自治和工人和农民翻身成为主人的两个原则之上。当然,民族地区该有多大的自治权,实际上又得到了多大的自治权都是受争论的话题,❲4❳民族矛盾在毛时代也没有完全消失,文革时期甚至还出现过要求民族独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5❳但尽管如此,毛时代相对和平的民族关系仍然反映在许多不同的个人回忆中。拜乐的一名维族采访对象,1974年作为红卫兵来到乌鲁木齐的阿弥尔,回忆到他当年很相信国家的方向,希望参与到其中。❲6❳拜乐的研究中也发现新疆的新老汉族移民对维族的态度不一样,老汉族移民甚至会责怪新移民破坏他们与维族同胞原来的和平相处。❲7❳就算毛时代的民族关系不完美,相比清朝的激烈民族压迫和如今重新出现的尖锐民族冲突,毛时代无疑是少数民族得到了相对平等的权力,民族关系相对和平的时代。
与之相比,80、90年代的新疆发生了多个民族冲突事件,民族关系迅速出现了紧张化。1980和1981年,南疆地区首先出现了三起大型冲突:1980年的阿克苏“4. 9” 事件,1981年的叶城“1. 13”事件,和1981年喀什“10. 30”事件。这其中每次事件均涉及2000-3000人上街游行、冲击政府机关、与警察打架等情况。事件导火索均为一些本地突发事件。阿克苏“4. 9”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一名酗酒的维族被汉族警察抓捕后,因被毛巾堵口窒息而死。叶城“1. 13”事件则因一清真寺失火爆发。而喀什“10. 30”事件是因一名汉族知青与在供销社当临时工的维族农民发生冲突,汉族知青用猎枪打死维族农民引发抗议。报道称这几场骚乱中出现“打倒黑大爷政府”和“伊斯兰共和国万岁”等口号。❲8❳
80年代中后期,则出现了一系列集中在乌鲁木齐的学生抗议。在1985年,因反对中央把民族干部司马义调到民委工作,2000多名新疆大学学生游行抗议。学生的诉求包括反对大汉主义,加强对民族教育的支持,反对计划生育,和反对在新疆做核试验等。混杂在其中也有新疆独立的口号。此后还有1988年,因厕所中发现侮辱性标语而引起的“6.15事件”,和1989年由一本自称描述穆斯林性习惯的耻辱性出版物引发的“5.19骚乱”。这些事件均发生在乌鲁木齐,以学生为核心群体。❲9❳
到了90年代,民族冲突再次在南疆的维族农村地带爆发。涉及200多名维族围攻乡政府的1990年巴仁乡事件为这个年代的民族冲突拉开了序幕。有记录把这次事件描述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精心组织的武装起义,也有人称事件是因维族对汉族迁入和对本地维族妇女被强制堕胎不满而爆发。❲10❳由于各版相关记录之间差异非常大,巴仁乡事件的真实起因难以判断。
在巴仁乡事件之后,新疆开始出现炸弹爆炸等恐怖袭击,也陆续出现95年和田暴乱和97年伊犁事件等大型冲突。在官方的叙事中,90年代越发频繁的民族冲突和恐怖事件越来越多受到有组织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影响。由于在2001年后,矛头指向有组织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可以让打压得到国际认可,这些描述的真实性需要警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90年代,新疆的民族矛盾变得更加严峻和广泛。这些越发频繁的民族冲突引来了国家第一次对新疆“分裂主义者”的集中打压:1996年的“严打”行动。❲11❳通过这一系列的冲突和随之而来的打压,90年代成为了新疆民族矛盾真正成型的年代。
曾经匿迹的新疆民族矛盾,为什么在80年代重新出现,在90年代广泛爆发?对此问题有多种解释。自由派给出的答案是文革的残酷打压压住了少数民族的声音,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声音才有机会爆发出来。但尤其在今天返回去看,这样的解释无法置信。如果新疆今天的强大技术监控和接近10%的穆斯林人口被关押在再教育营里都压不住民族矛盾,不靠武力,而靠群众监督的文革群众运动,是如何在当时汉族还不多的南疆压住民族冲突的?显然,自由派的解释行不通。其次,也有人指向由美帝扶持的阿富汗极端伊斯兰主义者的影响,苏联解体前夕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改革开放以后,被释放的新疆民族精英。这些因素可能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如果只有这些因素,没有民族矛盾的物资基础,民族冲突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边缘化现象。为什么是新疆,而不是当年同样有民族矛盾的西藏,成为今天中国民族矛盾最尖锐之处,又成为民族压迫最严峻的地方,这些都需要了解背后的社会基础。
民族矛盾之所以会在80年代出现,在90年代越发激烈,也不难找到的原因。80年代中后期的新疆学生运动,出现在全国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各种思想流派(和潜在阶级利益)争辩的80年代,因此不以为奇。同时,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不满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铁饭碗被瓦解的80年代,获得了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青年相比他们的汉族同胞更难以在私有市场上竞争,他们常常受到就业歧视。这一层被排挤的青年正是80年代中后期新疆学生运动的社会基础。然后,相比8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90年代出现的民族矛盾激烈化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国家在新疆推动的资源和经济开发,资本的洪流式侵入。
从圈地到民族起义
新疆改革开放时代的资本主义复辟,用官方自己的话,是一个“双向流动”过程。一边,有资本及其汉族代表涌入新疆圈地,一边有被边缘化的维族青年被半强制送往全国各地参与资本主义建设。而资本侵入给新疆带来的矛盾,无疑催化了新疆的民族矛盾,把新疆推向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局面。
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广为人知,但他的前身,1992年推动的西北开发,如今少有人提起。实际上,中央很早就把新疆定为一个改革开放蓝图下的重点发展区域。1992年的西北开发政策,指明了要开发新疆的自然资源,同时建立一个通往中亚的贸易中心。在改革开放和苏联解体的双重背景之下,偏远的新疆获得了两种新的经济意义。首先在国内出口加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新疆的能源和土地资源成为了制造业的重要后盾。在资本蓬勃发展的90年代,国家的能源需求快速上涨:1993年,中国成为了一个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年原油也开始净进口。❲12❳此时,拥有全国超过20%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新疆,成为了国家改革开放策略中关键的一环。而后,国家的经济规划师还盯上了新疆的辽阔土地,复制了苏联在中亚国家曾经实行过的棉花种植政策,给新疆提出了“一黑一白”的经济发展策略:一边开发油田,一边在新疆大量开荒,种植纺织业所需要的棉花。除了它的自然资源产地角色以外,新疆还被赋予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定位。苏联解体后,中国得到了新的机会跟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形成联盟。接壤中亚国家的新疆因此被视为发展对外贸易的关键地带。为了能源,为了农业原材料,以及为了与中亚的贸易关系,在90年代,国家开始大力推动新疆的经济开发。
在这样的推动之下,新疆的经济开始神速发展。1992年,新疆模仿着沿海省份,开始建设开发区,举办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同年,中央开始给新疆大量的财政拨款,也在新疆实施了跟沿海省份一样的分税制改革,以刺激地方政府搞市场建设的积极性。中央这些财政支持在新疆化为了许多基础建设项目,大大打开了曾经封闭的南疆维族家园。从1991到1994短短三年间,新疆的基础建设投资就从73亿元涨到了165亿,GDP也翻了一倍。大量汉族被经济机会吸引前来。90年代的新疆很快就成为了仅排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之后,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13❳

在毛时代,维族聚居的南疆,一直主要由维族自己居住和管理,汉族占人口的不到10%,当地的干部以维族为主。❲14❳虽然毛时代有不少汉族跟兵团转移到了新疆,但兵团主要入住的是人口稀少、属于军事要地的北疆。毛时代北疆和南疆相对割裂的发展模式也留下了潜在的矛盾,维族务农的南疆跟兵团开发的北疆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但直到80年代,这些差异貌似没有引发什么激烈的民族冲突。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则第一次让大量资本和汉族流入南疆,催化了民族冲突。新的基础建设开通了走进南疆维族家园的道路,但真正把人和资本吸引来的,是“一黑一白”两产业。在这两种产业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侵入与民族矛盾的关系。
首先开发的是石油产业。石油是南疆开发的关键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是80年代探明,1990年投入生产,位于南疆的塔里木油田。到90年代末,被着急开发的塔里木油田已经成为了全国第四大油田。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央92年推动西北开发是想通过经济发展回应新疆80年代出现的民族矛盾,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当年会选择了新疆(而不是西藏或其他当年也有民族冲突的地方)为首一个西部经济开发试验地。新疆被选为资本主义重点开发地,主要不是为了回应民族矛盾,而是因为它拥有重要的资源和策略性的地理位置。西北开发的几大基础建设项目也暗示了这一点:它们均与能源有关。这些项目包括穿越南疆新油田地带,1995年通车的塔里木沙漠公路;1999年开通,连接喀什噶尔市和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总部库尔勒市的新铁路;以及2002年开建、2004年完工,从新疆通往上海的西气东输管道工程。❲15❳可悲的是,这些大规模能源开发并没有给本地维族带来好处。相对高薪的能源行业工作把维族排除在外。这些行业很少聘用维族工人,反而把大量汉族工人带入南疆。这或许是因为在利润面前,资本顾不得以往的民族平等政策,直接聘用已有行业经验的汉族技术工,又或许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希望把石油等关键性行业留在汉族手中。无论如何,在2001年,新疆党委的民族问题课题小组反映,在自由市场的规律之下,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维族就业明显成为问题。❲16❳涌入新疆的诸多外来资本和人口把新疆的生活成本拉高,却没有帮助到维族。他们形成在维族原住民身边一个触不可及的富有阶层,然而大多数维族被排除在新的财富之外。
能源行业带来了新移民、工作歧视和以种族划分的贫富分化,但比起这些对城市维族的影响,能源行业的环境影响和新疆棉花政策带来的农村变化,对主要以务农为生的维族群体,伤害更为严重。80年代末开始蓬勃发展的能源行业本来就让新疆稀缺的水资源变得更紧张。国家的新疆棉花政策更让资源竞争变得激烈化。如果在资本主义初现的英国,资本家为了给纺织业提供了羊毛广泛圈地,那么在今天的新疆,资本家则是为纺织业圈地种植棉花。相关政策鼓励在新疆大量开荒种植棉花,为此工程提供了雄厚的财政补贴。但是这项政策的主要收益者,不是本地维族,而是被吸引前来开荒赚钱的汉族移民。1991至1997年间,新疆开辟了330万亩荒地,主要承包给汉族新移民来种植棉花。❲17❳这些新的棉花种植地集中在南疆维族地带。❲18❳1998年7月在新疆日报头版登报的一个小广告反映了当年的状况:广告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有5000亩可承包的新开荒田地,前两年免承包费。而当年的且末是一个人均土地不到2.5亩,水供应紧张的穷僻维族县。此地后来频繁因水源竞争和土地损坏问题发生汉族和维族社区之间的冲突。❲19❳
新疆的开发给很多奔疆参加棉花种植的汉人确实带来了好处:他们或当高薪季节工,或获得了廉价的土地和住房,或以大农场主的身份赚得盆满钵满。相反,在南疆的土地上世代为农的维族农民不仅没有受益,很多反而因新的政策成了棉花公司掌中的农奴,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他们跟汉族的农场主、农工不一样,不是奔着利润才来,也不能看到局势不好就甩手离开。棉花政策在他们身上化为政府官员用各种手段胁迫他们把原来丰富多样的作物统统改种棉花,然后命令他们以指定的价格卖给指定的国营公司。棉花小规模种植本就难以盈利,因此很多维族农民改种棉花后,收入不涨反降,同时因粮食等其他作物被棉花代替,维族农民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和被国营公司控制的销路。❲20❳
1990至1997年间,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翻了倍,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棉花产地,提供全国25%的棉花。随着棉花种植的增多,国家也开始鼓励纺织企业转移到新疆。如今,国内的棉花生产几乎由新疆独扛:84%的中国棉花都源于新疆。❲21❳新疆的棉花政策,耗干了维族故乡的自然资源,破坏了维族农民原来的生计和自给自足能力。这项政策跟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曾推行的单项经济作物种植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让新疆的生态和社会都变得脆弱、易碎,造成的伤害甚至比排挤维族,扩大贫富差距的能源行业还要大。
在新疆经济开发,石油和棉花“一黑一白”策略的影响之下,曾经属于维族自治的南疆地区涌入了前所未见的汉族移民潮。同时,一个以民族分层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开。在城镇非国营单位职工中,汉族工人的收入平均比维族工人高出52%。而城乡间,在全国已经悬殊的城乡贫富差距,在新疆更是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0%,以维族为主的农村人跟以汉族为主的城里人贫富差距越发鲜明。❲22❳新疆的维族原居民开始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不是主人,而是低人一等,被排挤在新型经济以外,被剥夺的底层。在城市,本地的高收入岗位,对维族不开放,甚至在国企里,都出现了“下岗先下维”的说法。维族被限于城市边缘的服务业经济。而在农村,维族身边的土地被大片大片承包给汉族新移民,已经稀缺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变得竞争越发激烈。越来越穷困的维族农民,看着日益发达的家乡,越来越看不到出路。这些,正是90年代新疆民族矛盾爆发的土壤。
在新疆党委民族问题课题组一份2001年的报告中,记录了这么一幕90年代末发生的“把民族自尊自信推到极端,排斥和歧视其他民族文化…… 片面评说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群众不满情绪”的事件:
1999年7、8月间,和田市(编者注:新疆最贫困的地区,当年占新疆63.3%的平困人口)斯地吐维清真寺哈提甫在一次周五礼拜时,当着3-4千教民的面说:‘维吾尔族妇女、青年因为失业而卖淫或成为流浪汉,让我们为了挽救他们祈祷吧!愿安拉拯救他们的灵魂,给他们工作吧!让我们用哭声感动安拉吧!”导致上千人嚎啕大哭。
这个场景,相信在正经历广泛下岗潮的90年代中国的许多地方都能引起共鸣。如果说宗教极端化,在东北一时盛行的法轮功也不无类似之处。而仅因为民族的差别,这些新疆少数民族的普遍不满被戴上了“极端民族自尊”的外衣。把资本矛盾推向民族化的有多种因素:即有私有资本的民族分化倾向(见第二章更深入的讨论),有各种利用民族矛盾的势力,也有资产阶级国家用以回应矛盾的民族压迫政策。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介绍民族矛盾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打压如何相互促进,发展为今天的局面。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形成民族压迫的规律性,以及资本与现有压迫方式的关系,则会留到后面的文章进一步分析。
从民族矛盾到集中营
从1996年初现的“严打”行动到今天遍布新疆的民族围剿系统,新疆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打压多年以来相互促进,同步升级。20多年来,1996年初现的民族压迫系统一直压制着在新疆的资本主义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原住民积累的不满。维稳系统防火员般地消灭着在干柴状的社会上不断燃起的火苗。随着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深,1996年的“严打”政策经历了两次升级。第一次是2009年的乌鲁木齐暴乱后,开始全方位建设的技术监控。这一次事件后,新疆被断了九个月的网。网络再次上线时,脸书、推特和其他国外社交媒体在墙内再也连不上了。第二次是2017年,“再教育”系统的诞生。此后,被拘禁的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牢笼成为了每家每户都近在眼前的威胁。
2009年的乌鲁木齐暴乱是新疆多年累计的民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它的直接起因是两名维族工人在韶关的一家工厂里被汉族工人打死。韶关事件的背景,则是2003年发起,新疆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联手,大量输送维族年轻劳动力到南方的工厂里工作的政策。❲23❳这项政策没有解决新疆本地的工作歧视问题,给维族创造更多的本地工作机会。正相反,它与那些鼓励汉族入驻新疆的政策同步执行。它虽然给了维族“剩余劳动力”一些工作机会,但这并不是慈善行为。这项把维族年轻人派到远方工作的政策,跟国企改革时派老干部出去“学习”有类似的药效,一边把可能反对新开发的老主人送得远远的,一边奋力输入支持新制度的新人来冲淡老人的影响力。
在输送政策的安排之下,2009年5月,全球最大玩具生产商旭日玩具的韶关工厂接收了800多名18至29岁的维族工人加入他们18000人的劳动大军。最初,汉族工人觉得喜欢唱歌跳舞来交友的维族工人很有趣,但是随着维族工人人数的增多,在汉维两族因语言问题无法沟通的情况之下,汉族工人对维族的负面印象开始越来越多。有一天,厂里开始广传几名维族男工强奸一名汉族女工的故事。此后,6月25日的深夜里,大量汉族工人聚起来开始殴打维族工人。持续了三个小时的冲突最后导致2名维族工人死亡,118人受伤。事件结束之后,维族工人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独立的厂区,与汉族工人隔离开。政府后来的通报称,没有发现任何强奸的证据,强奸故事由一名想报复工厂的被解雇工人编造。❲24❳而维族的社交媒体上则流传,事件是在汉族管理性骚扰维族女工时,因维族男工介入而起。❲25❳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常常受忽视的女性权益,工作场合里通常被默认甚至反过来责怪女性勾引人的性骚扰事件,为什么会引发两个民族之间的流血性冲突?这其中有种族歧视和沟通问题,但也有汉族和维族工人都藏在心里的重重不满和生活压力。这些压力和愤怒,正是资本主义皆对汉族和维族工人进行严重的压迫和剥削的产物。
韶关事件之后,在网络开始普及的2000年代末,年轻维族工人被汉族打死的消息很快传回到新疆。7月5日,很多维族走上乌鲁木齐的街头抗议。原本和平的游行抗议后来演变为暴力冲突:维族攻击汉族,汉族反击。官方消息称当天有184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包括汉族和维族。一个不确定真假的谣言引发了一系列的暴力冲突。这其中也有在新疆开发过程中,多年累计的不满和民族矛盾。这些矛盾在韶关事件的促进之下,爆发为广泛的血性冲突,以鲜血的洗礼把资本的圈地和剥削所引起的矛盾凝聚为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7月5日的乌鲁木齐暴乱带来了一场激烈的打压,其中包括警察广泛抓捕抗议者和受政府庇护的汉族自发报复维族。同时,政府便开始重视网络管控,找科技公司联手加强新疆的社会控制。政府因此邀请了许多科技公司以新疆为实验地,从事分析维族线上活动、研发新社会管控技术的工作。一个强大的网络和生物识别监控系统随后布开。2014年,新疆开始全面实施政府与科技公司合作创建的便民卡系统,让维族必须申请便民卡才可以出县,并且必须长期携带便民卡,允许警察随时扫码查看个人信息。以乌鲁木齐为例,只有10%的维族能成功申请到便民卡,❲26❳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被控制在县域内,无法跃出那些守着县界的检查站。新疆的农村因此得到“室外牢笼”的称呼。
在随后的几年里,少数民族越来越深的不满,日益加深的民族仇恨,开始溢出新疆的边界。2014年,三名维族开车闯入天安门广场,撞死了自己与路人,昆明火车站又出现了维族持刀袭击。这些绝望的举动,反社会行为,与2018年重庆公交司机载客坠江或这几年屡次出现的学校刀砍事件相比,没有什么太的不同,但是隔了一层不同的皮肤和语言,这些事件就成为了两个群体之间难以治愈的误解。同时,这些仇恨也被资本和资产阶级国家利用来分化无产阶级(见此系列第二篇)。汉族对维族的仇恨,让维族被孤立,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以更残酷地打压和剥削的超级剥削群体。
2017年,这种超常剥削和压迫以再教育营系统的形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陈全国的推动之下,新疆建立了一个让人难以思索的现代集中营体系。2016至2017年两年间,国家投入了72亿来建设新疆的信息安全行业,建设了总价值650亿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拨了1600亿给新疆地方政府,主要用以建设新的再教育营系统。很快,任何“异常”行为,从戒酒到反对征地,都成为了潜在恐怖主义倾向的表现,成为了被送进再教育营的原因。新疆的少数民族被分别关在室外和室内的牢笼里。资本不需要他们时,可以用这种超常最残酷的方法打压他们的反抗,当需要他们时,又可以动用为超常廉价又听话的劳动力(见此系列第三篇)。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讨论了新疆民族矛盾的根源,看到了资本主义在背后的催化作用。我们也浅层介绍了今天的民族围剿系统的发展过程。随后,这个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将进一步探讨民族和阶级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疆形成的关系。最后一篇则会试图分析新疆形成的监控和再教育营系统。
❲1❳BYLER, Darren. In the Camps: 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BYLER, Darren. Terror Capitalism: Uyghur Disposs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a Chinese C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2❳本文仅代表作者自己的分析,并不代表拜乐的意见。因为拜乐的著作里有较多对资本运作和阶级关系的关注,以及大量在近十年里收集的一手信息,为此系列文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启发,所以重点点明这两本书。
❲3❳新疆党委民族问题课题组,「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式下新疆民族问题的调查报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7)。
❲4❳民族自治政策之下培养的民族干部、实行的教育和就业上对少数民族照顾以及对民族语言的尊重等是有据可循的,但是什么是充分的自治,关于自治有过哪些争论或矛盾,作者凭仍然肤浅的研究无法说清楚。由于目前找到的关于毛时代新疆的资料也严重不足,并且认为在这一个本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上应该警惕过度美化毛时代,这里选择不做更多的推论。
❲5❳一个1968年成立,据说受到苏联一定支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公安1970年破获说涉及5000人。
❲6❳《恐怖资本主义》第六章中维族红卫兵阿弥尔(Emir)的故事。
❲7❳BYLER,2022.
❲8❳张运德,「乌鲁木齐“7•5”事件主要特点及其引发的意识形态几点思考」,《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2009年10月22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25203424/http://www.xjass.com/zxdt/content/2009-10/22/content_113270.htm
❲9❳TOOPS, Stanley, Understanding the disturbances in Xinjiang,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9 (https://www.e-ir.info/2009/07/09/understanding-the-xinjiang-disturbances-in-china/); CASTETS, Rémi, The Uyghurs in Xinjiang–The Malaise Grows, China perspectives, 2003, 49; GUO, 2015; 雨夹雪,「暴乱背后---浅谈“疆独”问题」,乌有之乡,2014年3月2日,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10/308142.html
❲10❳BYLER, 2021; CASTETS, 2003; GUO, 2015.
❲11❳CASTETS, 2003; GUO, 2015.
❲12❳BECQUELIN, Nicolas, Stage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The China Quarterly, 2004, 178: 358-378.
❲13❳BECQUELIN, Nicolas, Xinjiang in the Nineties, The China Journal, 2000, 44: 65-90.
❲14❳BYLER, 2021
❲15❳BEQUELIN, 2004; BYLER, 2022.
❲16❳新疆党委民族问题课题组,「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式下新疆民族问题的调查报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7)
❲17❳BEQUELIN, 2000.
❲18❳BYLER, 2022.
❲19❳BEQUELIN, 2000.
❲20❳BYLER, 2022.
❲21❳BYLER, 2022.
❲22❳BYLER, 2022.
❲23❳BYLER, 2022.
❲24❳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jul/10/china-riots-uighurs-han-urumqi
❲25❳BYLER, 2022.
❲26❳BYLER,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