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八分钟: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
蛋挞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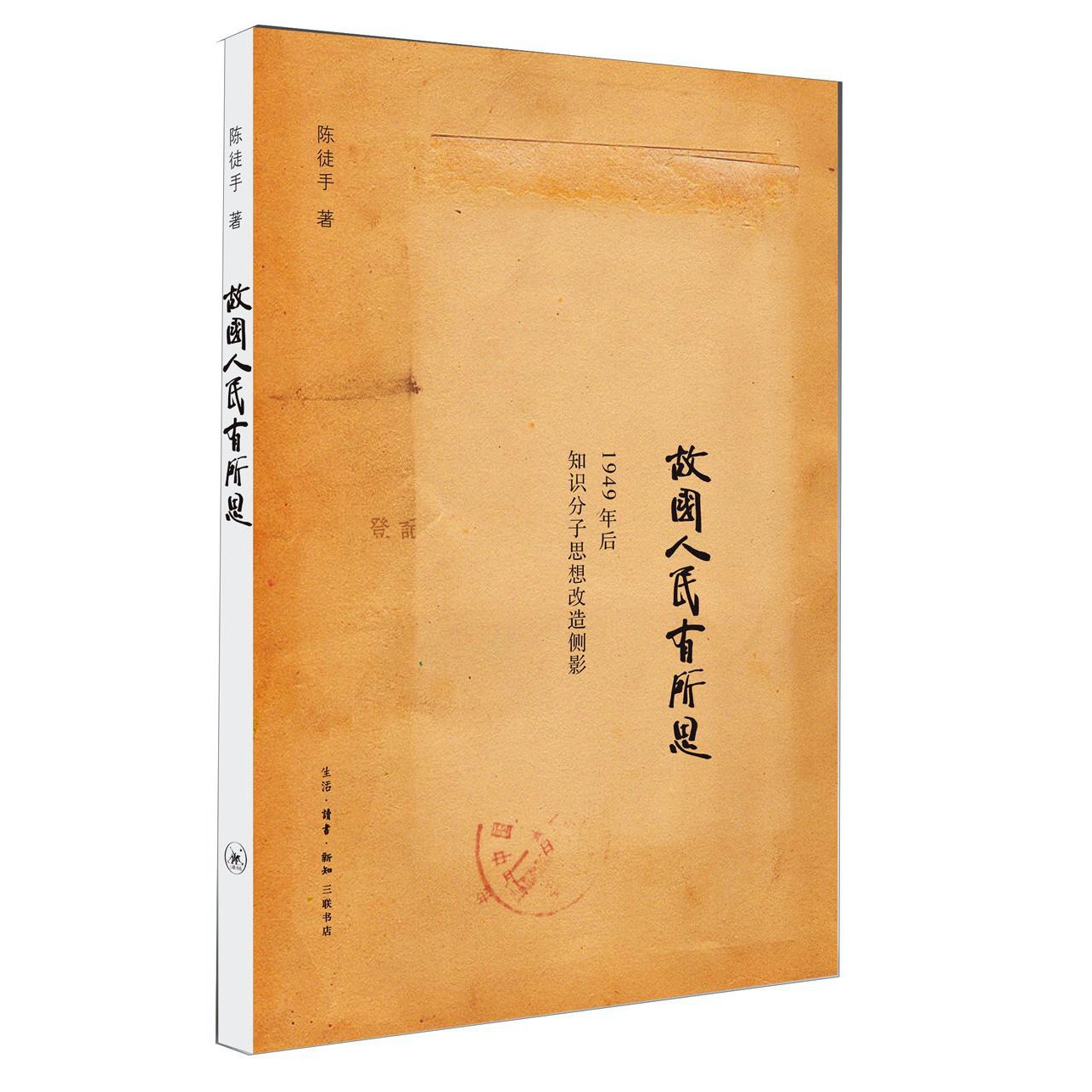
作者:梁文道
2014年3月21日
关于上个世纪建国初期到反右期间知识分子改造这些问题里面,很多的记载很多的书我们都已经看过很多了,但是去年出了一本书,非常受关注,就是我手上的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为什么他会这么受重视呢,正是因为他的作者陈徒手,用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12年的时间,才完成这本书,但这本书其实非常的薄,除了他写作很慢之外,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陈徒手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翻档案,所以这本书跟我刚才提到的大量去谈相同时期相同题材的那些书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陈徒手在这本书里面很少做太多的感情上面的描述,很少试图去深挖,尽管他有时候有这样的言语,但是他很少去深挖某一个知识分子,在经历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什么内心挣扎,他的痛苦,几乎是不太带情感的去说,有时候他会有一些价值跟情感的描述,但是没有把他写的太过的文学化甚至小说化。
第二就是他写的时候他也不太做太多非常的肯定的分析跟判断,所以他又跟很多学者比如说我们之前做过的像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不太一样,在那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严谨的分析跟推论,但是陈徒手往往只是试图依照时间的次序,把一些档案攫取出来,然后给我们看到一个故事的侧影,真的像这本书的书名讲的,他的侧影跟片段。
这么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这本书好像很枯燥,好像很冷淡,但其实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正正是因为陈徒手这样的写法,跟他给了数量不多,但是已经足够的一些的暗示,使得我们可以去关注到那些年代里面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里面某些大的趋势,跟一些超越了个人的面貌,第二,我觉得这本书的好处就是他能够让,我觉得陈徒手他是比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很多书,更加带着同情心回到那个年代,什么意思呢,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更年轻的朋友,不太能够了解,为什么那时候许多大名鼎鼎,今天我们重新挖出来都觉得是学术大师一代的思想巨星的人物,为什么那时候能够变得忽然没有风骨了,写一些那么幼稚的政治奉承的话,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开始觉得说你看这些人没骨头,没腰骨,中国文人就是怎么样,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说你看那时候的人还互相揭发互相批判互相出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容易我们对过去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的表现跟行为会发生一种道德上的要求跟谴责。
但是陈徒手也不做这个,他是试图回到那个时候,想像一下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侧影想像一下,如果你在那个具体环境,你又会怎么样,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里面,开篇的第一号人物就是俞平伯,俞平伯都不需要再多介绍,在这本书里面主要谈的是1954年的时候,俞平伯当时,因为他的红学研究被批判,然后谈慢慢怎么整个调整个过程,这里面他对俞平伯最后的总结最后的状况是这样的,他就说到俞平伯,本来是出了名的自由散漫的人,对工作抱着应付的态度,闲散就给香港大公报写写文章,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一开始他也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东西过不了关,为什么自己的东西会被批判的那么猛,他还觉得自己对,但是慢慢慢慢,他开始表达了他的想法了,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根据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学研究上落后于政治上的进步,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思想上还占统治地位,解放几年了,我还继续用索引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来研究学问,他就开始批判自己。
他批判完自己之后,后来很多人觉得他有进步,他再接再励,提出要整理研究杜甫和李白的诗,而且打算用集体讨论分工合作这种新的流行方式来逐步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后来他就说到,他说党总支,就是当时的北大党总支和俞平伯本人,都承认思想改造的艰苦程度,俞说这里好像通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中洋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而党总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学术批判中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丢掉的只是虚假的名誉,而得到的确是马列主义,那么后来何其芳在一个会议上总结,一个感慨,也说学术思想批判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索的工作也好做了,过去开会我发愁没人讲话,现在大家都积极发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向来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后也变得爱唠叨,说的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那么诚恳和老实。
其实同样老实的人,也还有很多,比如说原来当鲁汶大学校长,后来建国后专任北师大校长的 陈元 (音),一代历史学的大宗师,他也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比如说他说他当时50年代头的时候,他报名参加西南土地改革运动,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学术思路,比如说在四川巴县乡间应邀参加斗争地主大会,做了革命性较强的发言,他在当地干部陪同下到处走访,实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这时候有趣的来了,他发现这些碑上写的东西跟斗争大会上面听到的什么地主剥削的残酷事实不符,按照他过去的习惯,他会说那么这些碑文上所讲的东西恐怕才是真的吧,那些大会上说的东西可能是政治的虚构吧,但这时候他不这么想,他想到的只是过去自己只懂得研究晶石碑文,为什么从来不太记载劳动人民被压迫的情况呢,由此他对以往闭门自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过了不久,校党委欣喜的向市委汇报说陈元已经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批判,你看,陈元他懂得反省了。
建国初年到50年代头的时候,我们中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面其中有很重要的地方,就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安排他们怎么样分配他们,他们有很多人就像我们昨天提到陈垣,他在民国年代已经是有名的大学者,而且已经担当了学校的行政工作,那么做到了校长教务长的人在所多有,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整个高等教育的制度变了,他实际上由党来领导,由党委书记,那么原来的学校没有党委书记只有校长,现在有党委书记来了,下面有党委组织了,到底这个权力该怎么分配怎么平衡,中间又会不会出现问题跟摩擦呢。
那么在陈徒手这本写的相当精简的《故国人民有所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里面提到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他不是重点去谈马寅初怎么样因为坚持自己的人口论,而被批判,他谈陈垣的时候谈周培源的时候,也没有谈太多,当然也会触及到他们的思想学术思想的问题,但是常常也会碰到他们实际工作上面的状况,那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描述的情况,这到底校长是干吗的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连马寅初当北大校长,他在北大他们创刊了一份新的学报,他登一篇文章居然都分不出去,他在北大当校长当的是窝囊到什么地步呢,是学校里面随便换什么系主任也都不需要经过他,因为全部都有党委管着,那么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有怨言,这个怨言就是你党委到底应该管什么,你管政治管思想,但是你这个连具体的教学学术研究你都管,你懂吗,你是个外行人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不能够外行领导内行,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大家可不是这么想,大家会觉得说就因为你学术上面有这些封建的过去封建的一些的余孽或者资产阶级的余毒在,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教授现在都应该是被好好的修整一下,好好的改造一下,甚至该被斗倒的,最起码不要把他们当成大牌,不要把他们看的太神圣,那时候把他们看的太大牌都是个问题。
比如说马寅初去修建大坝的,当时一些的十三陵水库的一些工程上面看望的时候,他的学生北大学生看到他很高兴,马校长来说了就说向马老学习,说希望将来我们也能够有机会像有马老那么大的学问,这些事情被党委他们的人看到就很不妙了,他们就会说可见过去这些老学者思想上还在毒化新一代的年轻人,所以他们要培养的是年轻人不服输,看到这些老学者老教授不用太瞧得起他们的气派来。
而这时候就有很多瞎指挥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当时头号大物理学家,流体物理学第一人周培源,他在这边他就说到,1962年形势缓和的时候,他恼怒的提及当年大批判令人伤心的往事,他说那个时候批判量子力学,不讲好科学,居然是讲哲学问题,然后说什么比如说他做流体力学,有同学批判他,说他这个流体力学与实践不符,是违心主义,他说这些东西简直是瞎搞,完全是很粗暴的运动,但是这时候甚至你就看到了,在党委的那些外行的指挥下面,只过问政治,不管学术,但是他偏偏要管到学术上面来谈政治的时候,教学上面谈政治的时候,会出很多问题,那么于是有的学者就干脆就什么事儿都主动的不管,撒手一边去,有的就表现出很乖很顺从的样子,也有的还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像周培源,周培源是另一种情况,由于他在国际上太著名了太大牌了,所以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形象学术界的形象代言人,他反而担任了很多很实际的工作,这些实际的工作就包括这位新中国的物理学界的形象代言人,到处飞到处跑,常常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国外,那么慢慢慢慢他觉得自己学问没做好,已经开始落后,他非常担心,所以他是怎么样,他跟那些因为政治不过关而什么事实事儿都不用干的所谓的校领导学者不一样,他是一个学者,他想做学问,但因为他的形象却反而变得他没工夫做学问,一天到晚要忙着搞实物,后来被迫要辞职。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很重要的学者,他们当时在改造运动的过程里面,他们的整个挣扎反复是怎么样,比如说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像冯友兰这些大学者,那么这些人物我们现在看到冯友兰他当时的状况远远比我们想像的要麻烦,要复杂,那个时候被人出卖或出卖人都不能够用今天的标准来理解,为什么,那时候你想想看,在一些批斗大会上面,鼓动你的好朋友好同事好学生出来揭发你私下说的话,这种东西在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你怎么能够把人私下聊的事情拿出来这么当一个人的罪证,这很不象话,但是当时说这些话却是被鼓励的,被认为说正当的,而说这些话的人很奇怪,他会反过来觉得舒服了,他觉得你看我说了一些揭发了我朋友的隐私出来,大家赞赏,我好像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情,舒服了,而这时候大家又对我温暖了,这时候他们这个感慨觉得你们对我真好,这么温暖还鼓励我给我掌声,所以很多人在经历过这样的揭发朋友隐私的事之后,他们就会说你看中国有史以来对知识分子最关怀的莫过于共产党了,这时候这种感慨出来恐怕是很真心的感慨,而这个感慨就是当时发生在傅英(音)身上的事,是那些攻击他的人把他的私下的言谈揭发出来就这种感慨,而傅英是谁呢?是当时有名的中右派标兵,什么叫中右呢,就是他不算完全的右派,他是中间亲右,这是个 毛泽东 亲自钦定的一个中右标兵,那么也就说右派标准以他的言论为界,过了他就叫右了。
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没有他右,都也被划成右派,所以其实这个划法是保护了傅英,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要大搞他,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一个本来决定不要大搞的人,到了后面也会被斗的很惨呢,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接着谈。
我们仍然给大家介绍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这本书,就像我昨天跟前天跟大家讲的,他用语很精简,他描述一个人的故事真的就只是个侧影,所以他没有太多的历史背景大环境大脉络的一个分析交代,对于一个人物完整的故事的前前后后也说的不多,所以有时候他很考验读者,就你这个读者,如果你对那个时代有些了解,或者对他所说的人物有些了解,看起来感觉会很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仍然侧重的是他这书提出了几个当时的一些共通的趋势跟线索,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我们继续讲讲傅英,傅英是1950年建国后一年从美国赶回来参与国家工作的化学专家,非常有名,在北大化学系教书,后来来当过副校长,我们昨天讲了,他被 毛泽东 钦定为中右的标兵,本来是能够把他保护起来或者不要太过分,但是他所在的北大化学系党总支却在之后接近4年的时间里面始终认为,这尽管上头毛已经定了他是中右,但下头仍然坚持认为他是没有戴帽子的右派,他们很多人坚持认为他就是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是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后来就只好一次又一次的不管上头的意见,继续揭发他继续批判他,而当时他们甚至又像我们前天所讲的,用来证明他这个人有问题的一个证据之一是什么呢,是这样的,说当时曾经有学生上课说,在下课之后跟同学们聊天说了这么一句话,哎,我们奋斗一生能够学到傅英先生的十分之一就很好了,为什么这句话都能够证明他是个右派呢,这句话是用来说明他让他的学生受到了迷惑,让他的学生中了毒,认为他是不可超越的。
所以后来调整专业方向的时候,不详经考虑就断然取消他领导的胶体化学教研室,这种情况在当时看起来是十分常见的,后面再加上他又谈了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说他说当时大跃进的时候,化学系在报告里面说他们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的科研项目,傅英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他好几次向校方提意见说,根据系里教师的力量水平,一年内完成几项就很不错了,有时纯化一个原料也得要三个月的时间,两到三个月怎么能够完成几百项呢,这些数字层层上报领导无法核对,这样的献礼够严肃吗。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非常有问题,但是后来还是没办法,后来慢慢的大家要把他,他的系的党部就是要把他变成一个负面的代表人物,要树立对立面,所以当时让一批学有所成的老教授和一些刚刚毕业甚至还在念书的青年师生分别编写讲义,比比看谁写的好,谁写的厉害,那么(00:03:41)教授,当时半导体化学教研室一位团员大声的对资深教授唐有祺宣布,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后来他们要编写的讲义,其中一篇讲义叫红色化学热力学,请注意,并不是说有一门化学学问叫红色化学热力学,这红色指的就是政治,就说化学热力学这本讲义是依照红色观点来写的,当时参与的同学就提出了,我们苦战一夜就写出了大纲,傅英觉得很惊讶,一夜搞出来不容易啊,觉得你们一天晚上就能够写出一个教学大纲,我这个老先生很佩服,真是不如你们,而这种情况我们在后面还看到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像王尧或者是还有一些别的学者,他们都谈到了当时的很多学生,几乎是不学无术,你也很难去教书,都不知道这个书该怎么教才好。
比如说他讲,他说现在考试前同学先要复习提纲,然后要指明重点,有了重点又要求先生讲出简明扼要的答案,那为什么学生,你要考试学生还叫你考前给出简明扼要的答案,这怎么行呢,他不能不行,为什么呢,王尧这位教文学的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就说,我们不敢出偏题,出的题目是重点而又重点,又都是理论化,因此考试总成绩是5分,但是问题是这些学生学了半天文学史,居然不知道律诗有八句,他说过去我们做老师的可以毫无顾忌的对学生谈自己的体会,现在我与学生个别接触,就很戒备,说不定哪一次接触他说你给他散布了资产阶级影响,要来批判你,两个人的谈话无从查对,一揭发出来无论如何大家都说学生总是对的,你只有检讨权没有解释权,而越解释越糟糕,本来三篇文章批判你,最后变成三十篇。
更好笑的例子发生在蔡旭的身上,就当年的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学系主任,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农学家,我们直到今天都还受惠于他的一些小麦品种的培育的研究,那么那个时候北京农业大学是出了名的左,就算有一些学者,像他们的学校已经被认为太左,把一些人给搞走了,要他们别再那样,但他们就是忍不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往左搞,然后在这时候反而有些想维护的学校教授的老领导就会被认为很不积极,像这个小麦王,当时有名的小麦王,他就觉得看到大跃进的时候报纸上面登的说亩产3530斤,他觉得很不可信,于是当然就要被批判,后来还被迫的要有别的学校提出说人家可以亩产8000斤,那么他就说好吧,他代表他学校应战,要比谁厉害,他说我们能够亩产8100斤,结果校方大为不快,党总支再三逼迫下,又涨到了8500斤,那么这些荒谬的故事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在这里面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说当时原来很多运动就算上头就算是毛他有时候觉得不要太过分,只要收一收,下面收不住,中宣部说不要搞的太过分,中央说不要搞的太过分,校的党委书记就要搞厉害,校党委书记说你们也别把这个人斗的太惨了,结果系里面的党书记就要把他弄下去,这什么意思呢,说明了就是某种斗争的势头已成,某种左倾的倾向一旦形成之后,他很难制止住,大家几乎是自动化的继续往那个方向发展,我们这本书就看到了多少知识分子,就几乎是在这种自动化的斗争环境之中一一被改造成功。
资料来源:凤凰读书
http://book.ifeng.com/kaijuanbafenzhong/wendang/detail_2014_03/21/35007230_0.shtml
http://book.ifeng.com/kaijuanbafenzhong/wendang/detail_2014_03/21/35007356_0.shtml
http://book.ifeng.com/kaijuanbafenzhong/wendang/detail_2014_03/24/35074088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