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生理性别?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酷儿理论|马各庄茶馆
Matters主讲/DT君
讨论者/马各庄村民
编者按:承接上期推送,我们继续刊登酷儿理论讲座第一讲其余部分。在进入多少有些晦涩的理论世界前,我们想先澄清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理解酷儿理论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次,我们想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始终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理解酷儿理论;第三,我们将从一个问题出发讨论一个略微晦涩的概念“操演性”,不过不用担心,这个概念没有听上去那么难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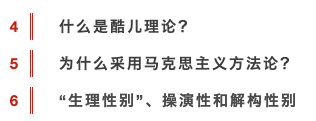
四、什么是酷儿理论?
< Q1 为什么酷儿理论看起来这么晦涩?>
诸位大概已经读过我的讲稿,可能会觉得不是很好读,这个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一定程度上是我的锅。考虑到它会作为以后讨论的底稿,我不想把它写的太简略。而是尽可能全面严谨一些。这样在以后的讨论当中,能讨论的方面它都会能够照顾到、能够提供一些参考,但是这样就会让它变得不好读。
其次,酷儿理论文本本身也具有晦涩难懂这个特点。我们说酷儿理论属于西方左翼思潮里面的“后现代”部分,而这个理论分支底下的那些文本本身就不好读。从历史来说,酷儿理论的出现是西方的左翼思想学院化的一个产物。当西方左翼运动进展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左翼理论渐渐不再能够引领社会运动的潮流,而只能跟在实践的后面。这时,有些理论家把当时逐渐兴起的所谓“后学”应用到性别研究上面,他们试图对现实当中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一种学院式的回应。这样,我们才有了叫做酷儿理论的这个东西。
尽管现实的社会运动发展得比他们更快,这个理论被发展出来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些后学理论家对于性别规范的运作机制提供了一些洞见。我认为这些洞见值得我们看一看,但我们没有必要花太多的精力去读他们的原著。因为那些书并不那么值得细读。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我觉得稍微花些时间——比如一两个星期——去看看他们的这些术语都是什么意思,也就够了。我认为,我们从酷儿理论里面能学到的更多的是描述跟性别有关的社会现象的语言,有些现象经由这么一说可以拎得比较清楚。 至于他们语义里边那些特别细微的东西,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辨析——那些东西都应该被翻译成人话,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 Q2 什么是酷儿,什么又是酷儿理论?>
酷儿(Queer)的中文翻译看上去很酷,但是queer这个词在英语里边其实是个骂人的词,它本来的意思是异常和变态,而且可能专门只跟性有关的那些变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剧叫Queer as Folk。这个剧有一个英版有一个美版,它的中译名叫《同志亦凡人》,翻译挺文雅的,但如果贴合它在英语语境的意思的话,至少得翻译成“变态也是人”。 总之Queer不是一个很好听的词。它本来指涉的就是一些反规范的性行为。一般说来,它指的可能是所谓的“异装”或者是喜欢同性,或者是所谓的自己对自己性别的认知和自己被指定的生理性别不符等等。
酷儿理论这个词所指的并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把后学思潮应用在性别研究上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冠着酷儿理论这个名义的东西,它们取向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张力。有些研究跟性别有关的亚文化现象,比如说当时还没有得到很合法承认的异装舞会,或者是跟性少数与跨性别有关的题材的文艺作品。还有一些去研究性欲生成的机制,这些就偏向实证一点的性别研究。还有一些人会去研究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总之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取向。
像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没有包括特别偏文化研究的东西,而是试图把这个跟性别有关的话题放回到一个更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之下。在整套讲座中,我们去研究,这些跟性别有关的规范在历史上是怎么生成的、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会特别关注:这些性别规范,在日常的运作当中,它是怎么体现出一种压迫性的权力关系?
五、为什么要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 Q1 我们要关心文艺批评吗?>
我个人认为我们不用花很多的精力去关注那些跟文艺研究有关的东西。举个例子,很多研究者会跑去对一个一个文艺作品去进行精神分析,研究里面什么东西体现了性别歧视。如果非要我关心这种话题的话,我也得关心它在实证层面引起的反应。首先创作它的人是否有这样的有意识的性别歧视的动机,或者是否有性别歧视的无意识?其次,这些所谓性别歧视的东西,究竟有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产生了哪种影响?是真的对观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还是观众看过之后就忘了?
这些问题不是你在这对文本做精神分析就能得到答案的。你必须要去实际的调查观众的反应,你必须要去实际跟踪看过这些东西之后,观众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观众会不会接受那种性别化的无意识。但这个就不是传统的文艺研究的路数。它所需要的实证调查是非常精密且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能够口头讨论清楚的东西。
< Q2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在这能够讨论清楚的,是跟性别有关那些规范生成的历史。我们看看我们手头的历史材料能够让我们对此做出什么样的结论,然后我们看看这些性别规范运作的压迫性,它在哪些地方能够明显的体现出来。我们在很多地方其实能看到比文艺作品要明显的多的压迫的体现。我们去看看这些暴力压迫性的规范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在历史上对于这些暴力和压迫的反抗,又是怎么运作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检视那些习以为常的性别规范。但是我们检视的方式是去追溯规范的历史。如果你追溯规范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些规范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它是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出现的。这个历史的演进本身就是权力关系当中不同的人们的斗争所推动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我们会说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最根本的推进力。我们为了批判性的检视这些性别规范,也就需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到与性别有关的那些斗争当中去。比如说争取女性工作权益的斗争,反对歧视的斗争(不管是对女性的歧视,还是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或者是反对性别暴力的斗争。我们只有参与进去之后,才能够知道这些规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运作,会和怎样的体制性暴力结合起来。这个是我认为学习酷儿理论应该遵循的路径。
< Q3 为什么要结合马克思?>
酷儿理论,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把后学的这种理念应用在性别研究上所得到的某种思潮。它大概兴起于90年代。在这我不打算过多的去叙述那些后学的观念,只是既然酷儿理论发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那些后学的东西多多少少得提一点,但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面。
我想要把后学往前去推一推——我觉得作为一种学院左翼的娱乐,后学在很多地方走得太远——我想要往回去追溯一些更加实证的、更加唯物主义的、更加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后学可以算进批判理论的脉络里面。一般会认为批判理论的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也好,后结构主义理论也好,它们是从批判理论的理论脉络里产生出来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是受马克思主义强烈影响才出现的一种社会理论。它的源头我们一般会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们最早把“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对立起来,做成一种社会理论。后来的微观暴力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关系不大,但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一直是既有对话也有张力。
第二,从社会斗争史上来说,跟性别有关的社会斗争,从来都与社会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者在今天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要太沾沾自喜,说“马克思主义者们领导了妇女解放运动或者领导了同性恋解放运动”。在历史上,这两家的关系要更加复杂。但确实,至少马克思主义为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曾经提供过激进的动能,在我们叙述社会运动史的时候是不可回避的。
第三,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马克思主义话语不仅对现实是强有力的批判武器,也很契合在中文世界做事情的需要。我们在中文世界里面会发现,在政府、官方所使用的话语中,他们不敢轻易地放弃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重新去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里面的那些激进的潜能,如果我们去提及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社会运动史上,那些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形成一种比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更加强大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今天的中国官方所不敢轻易放弃的一套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来的价值观那里去。马克思主义本来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为了被剥削、被压迫的人群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去斗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内蕴的价值取向。我们要理直气壮的提到这一点。可以预想的是,它在中国的言论场上肯定会更加有力的。
六、什么是生理性别、操演性和如何解构性别
< Q1 生理和社会性别二分有什么问题? >
我觉得大家肯定多少都听过两个词,一个词叫生理性别sex,一个叫社会性别gender。我们还会很熟悉这套话语,所谓的生理性别是你的外生殖器的形态,是你一出生的时候,根据你的外生殖器形态确定你被指派的性别:你是男的或者女的,或者是间性的,或者是性别不定的,它是所谓社会性别得以建构的基础。 社会性别是一种基于生理、性别建构起来的东西。生理性别是物质、自然的;社会性别是意识的、社会的。人们是在社会性别的基础之上,才讨论你的社会性别认同:你的性取向是什么。由此产生一大堆的分类:什么我生理性别男我性取向女,或者我的生理性别男我的心理性别女,或者我的生理性别女我的心理性别男,如此这般一大堆。

但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个家伙,可能确实是历史上第一个往另一个方向想的人,她说,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本身可能并不能分开。我们现在对于社会性别所有的讨论和观念都有一个基础:它假定了某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模拟关系。我们会觉得社会性别是一种像镜子一样反映生理性别的东西。也就是说关于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这种比较通行的二分里边,它假定了生理性别是一种自然出现的东西,然后把生理性别当作基础去雕刻你的社会性别。但是巴特勒说这种自然和社会的二分,可能本身也是一种观念的产物。它从来就不是自己就出现,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
我们能够指涉某个「特定」的生理性别或者某个「特定」的社会性别,而不探究生理性别和 /或社会性别是如何给定、通过什么手段给定的吗?而「生理性别」又是什么?它是自然的,是解剖学的,是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要如何评估企图为我们建立这些「事实」的科学话语?生理性别有没有历史?是否每一种生理性别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或者多个历史?是否有一种关于性别二分如何建立的历史,是否有一种显示出这种二元选项是可变建构的谱系学?由不同的科学话语所生产的、关于生理性别的那些表面上是自然的事实,是否在为其它的政治或者社会利益服务?如果生理性别的不可变性受到了挑战,那么也许这个称为「生理性别」的建构跟社会性别一样都是文化建构的;的确,也许它一直就是社会性别,而作为结果,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区别。
……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性别仅仅看作是文化在某种先在的生理性别上铭刻的意义(一种法律的概念);社会性别也必定指向生理性别本身能够建立的那个生产机制。结果是,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关系并不像文化之于自然那样;社会性别也是话语/文化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生理性别化的自然」或者「自然的生理性别」得以生产,并且被建构为前话语的、先于文化的,成为一种政治中立的表面,任由文化在其上作为。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第二版有中译本: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宋素凤译,三联书店(2009)pp.9-10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性别麻烦》这本书里面她有一连串的质询。当然这个家伙写东西一直都很绕。大概概括一下她想问的问题:生理性别这个概念真的有人们所设想的那么自然吗?把她这一大段话翻译成人话,她想说的是:你不可能脱离开你所处的语境,去谈论超脱于你的一种所谓“生理性别”。你谈论生理、性别,你就需要说话,你需要依赖于你所在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对于生理性别的描述和相关观念,与那种生理构造的差别之间,并不能够自然的衔接在一起——这个东西总是有一个社会和历史的背景。
人类进行繁殖的方式是有性生殖。但进行有性生殖,你不能一个人生,你需要两个不同的个体和两套不同的器官。我们把这些器官命名为生殖器,把生殖器按照它的形态和功能去进行分类。但这种分类的意识,是跟外生殖器的形态有某种本质的关联的吗? 好像也不是这样吧。这些器官本身并不仅仅有直接的生殖的功能,对吧?比如说卵巢,我们从生理学会知道卵巢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制造卵子,它也有别的生理功能,比如主要分泌雌性激素以及分泌少量雄性激素等等。雌性激素的生理功能也不止是和女性性征有关的那些。我们为什么单独把产生卵子功能抽出来,然后给它起名叫卵巢,认为它是一个生殖器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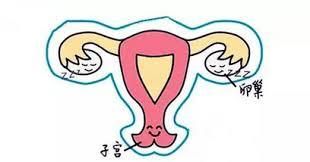
我们不在这里去纠结给它起这个名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要把——之所以给它起这个名字、之所以把这些跟生育繁衍有关的那部分功能抽出来认为它们是最重要的——背后这个思维方式单拎出来,我们看看这种思维方式是怎么形成的。好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留在后面再讨论。但首先我们要指出:人们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自然的东西。
Authracis 我不太理解。对于生殖系统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器官,它甚至上是演化上一个天然的分类。我觉得我没有太理解你想表达什么?
DT君 我的意思是,我们给它分类的标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我们对它的描述、我们叙述这些器官生理功能的方式,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橘子酱 我觉得刚刚举的卵巢例子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它叫卵巢?为什么在那么多功能里面单单挑出这样一个跟生殖直接有关的功能来讲?
林克斯 这或许是因为认识有先后,一开始你可能只认识到它可以产生卵子,后面……这个例子本身可能不太到位,有可能它后面才会被认识到有别的生理功能。如果你要追寻这些生理器官名词的来源的话,我觉得你得追寻到非常久以前。因为这种学术性的词汇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它原来所代表的那个意思、它命名的那个时代背景已被冲淡很多了。
DT君 可能还是阴茎或者阴道的例子比较到位。我们认为它们是外生殖器(external genitalia)的一部分,但性快感的功能是怎么和“生殖功能”绑定起来的?有性生殖的哺乳动物也不一定是在进行有性生殖的时候才使用这些器官,许多哺乳动物(自然包括人类)都会单纯为了快感去使用它们。我们是怎么把这两种功能绑定起来的?
Authracis 说一个题外话,我们可以去看昆虫器官的命名。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按照人类器官的命名推过去的。比如说人类的雄性外生殖器叫阴茎,有些昆虫的雄性外生殖器叫做阳茎……你会发现其他动物的命名也大致相似。因为最早的解剖学实践是在人类身上做的一些研究,等动物的解剖学发展起来后,他们直接把人类身上的一些东西给推演过去了。
DT君 是的,是以人类为模板。
Kyle 刚刚DT君讲到分类学本身要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是不是暗示着我们可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审视人类的分类学?想象一个不存在外生殖器维度性别的一个社会?我们目前的分类本身的确也会有很多模糊地带……但我觉得这种想想有一点困难,因为好像我们总还是能去分类。外生殖器形态总是能够去看出一个区别——除了少数在中间地带——人类社会绝大多数个体还是可以归为两极……
DT君 我觉得有些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否认有生理基础这回事的存在。我们绝对不能否认有生理基础这回事存在。但我们要指出的是:生理基础到社会分工中间经过了无数步的调整。
Authracis 我同意DT君的说法,但是我觉得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不是很恰当,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讨论的话,应该去想它最早器官是怎么被发现了或命名的,就像是有一种像是科学史或者说医学史……不过我想问一下,巴特勒的理论是否认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吗?
DT君 她自己肯定不会写这么傻的话。但是,我觉得后续受她影响的写作很多会有这个倾向。就你想巴特勒是比较文学系的。她还是比较喜欢说一些不太接地气的——仿佛“提着头发飞向太空”——的话。就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的意思。因为在过去关于性别的讨论里面,生理基础占的分量太大,所以当她试图拨乱反正,可能多少有点走过。
Kyle 我可不可以理解,她是在质疑或在怀疑,我们在讨论生理性别时所使用的这一系列语言和术语,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
DT君 对。她的意思是:我们使用的这些语言本身并非政治中立。我引用了她这一段话里面有一句,我给大家圈出来:由不同的科学话语所生产的、关于生理性别的那些表面上是自然的事实,是否在为其它的政治或者社会利益服务?
Kyle 所以“生理性别”这个术语本身其实不需要去那么严格的去审视……?
DT君 是的,我们是得继续使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同时也得意识到它所涵盖的意思,可能并非是如其表面那么中立。我们不必纠结到底“应该”使用哪个词,但我们可以以这个词为切口,去看看那些那些社会关系或者思想观念当中所蕴含的权力运作机制。
巴特勒写这些东西、思考这些问题,是受了当时的学院左翼潮流的影响。她的很大一部思想基础来自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这种思维方式很有启发性,但是对于我们的现实斗争来说,我觉得你不能太把它当真,你不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东西里去。 它能为我们提供的启发是:语言,也是一个可以透视权力机制的窗口——它并不如它表面上那么政治中立。
< Q2 性别是人有意识地表演出来的吗? >
在《性别麻烦》这本书里面最著名的概念,可能就是所谓的Performativity,操演性。
在比较先锋的女权或同性恋解放运动里,这个术语可能会被创造性误读成“性别是一种表演”。Performativity和Performance在拼法上确实很像,它们是同一个词根,但它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要想表演的话,你需要有一个主体,一个行使动作的人,TA能够自己选择——可能不完全自愿——但TA能够自己选择自己是个什么性别,然后去把这个性别演出来。但巴特勒传达的恰恰不是“性别是表演出来的”这个意思。她想说的是,这个“演”需要依照规范。TA在性别这件事情上并不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我能够选择某些事情”,恰恰相反,TA的操演需要得到外在性别规范的授权的。当然Performativity这个词在现实社会运动当中被怎么样理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这说的是巴特勒自己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她是什么意思。

她引用了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的一个概念。奥斯丁作了一个分类:你表述一个句子,这个动作会产生两种的可能效果。一种是descriptive,描述性的,比如说我举起一朵花说这是一朵花,这是一个描述性的行为。另一种是performative,述行性的,比如有一个牧师在教堂里边,对一对新人说“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我们看“牧师宣布新人结为夫妻”这个行为是怎么回事?首先牧师得到了某种官方授权,官方授权牧师去宣布这对新人结为夫妻。其次,通过牧师的宣布,这对新人之间,他们与婚姻有关的那些行为就得到了法律的授权,就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从此就可以援引和婚姻有关的法律制度和习俗来做事。牧师在这里的宣布就起到了一个授权的作用。那么这种行为就是perform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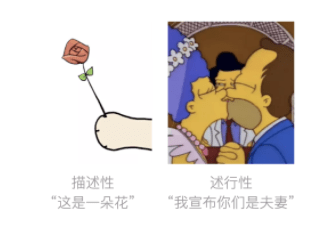
那么巴特勒把它引用过来,说性别的确认需要借助某种外在于你的规范。这个外在于你的规范规定了人的哪些生理特征是“性别的”,哪些行动、哪些仪式是和性别有关的,你做出哪些行动才能够被外在于你的规范确认为你是这种性别。但是你执行某些表演仪式,并不是由你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你在援引他、你在执行它——你在执行某种已经规定好的东西。你做的这个动作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你所处的社会环境规定的。
那么如果把她说的话拆到这一层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好像也没说什么。她所说的无非是性别规范是社会的,对吧?这个人写东西是很绕的,不要被她写的东西给骗了。她想表达的意思常常其实很简单。
< Q3 为什么语言哲学会处理这个? >
DT君 语言哲学就是要处理这个。可能从索绪尔(Saussure)那会对语言和言语作出区分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得处理这个。

林克斯 某些语法上可能是正确的词汇,比如说一个红绿色的猪,但是由于它和我们的直观经验如此相违背,以至于我们不能理解它背后的意思。我理解你说的述行性performative这个词指的是,比如说“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我们之所以能理解“宣布”,是因为有一套规范在支撑着它。如果没有这套规范的话,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荒谬的、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词语。
DT君 对,是这个意思。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不是一个牧师来说这句话,而是一个其他的人——比如一个马戏团里的小丑来说“宣布”,就是没有意义的。
林克斯 所以按巴特勒说的,性别本身也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如果没有这套规范,它本身就是一个空洞的……
DT君 空能指。跟性别有关的概念要发生作用,必须得有一个定义性别的场域。
Kyle 我继续好奇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关于“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的论述 ?
DT君 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这个问题特别好。第二讲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我们需要性别。
林克斯 生物上的话有性生殖是一个算是生物进化的选择吧?Authracis可能会熟悉。
DT君 不同物种的有性生殖虽然都被叫做有性生殖,但你细究起来这个机制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知道说有些爬行动物,它的幼体的性别是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当我们说海龟的性别的时候,它所指涉的东西跟人的性别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们其实还是在以人类的性别去model海龟的性别。不过“为什么需要性别”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划分不同的性别角色”为什么对于社会成了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对这个问题会给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 Q4 性别的本质是什么? >
书归正传!总之,删掉巴特勒的废话,我们可以提炼出理论的核心意思:
- 性别不是一个自然的、纯生理的东西;
- 跟性别有关的观念和话语需要一套社会规范来建立;
- 我们从性别规范中去援引一些符号、执行它规定的仪式,来不断的生产、塑造我们的性别身份,这就是我们性别的来源,我们需要日复一日不断的重复它。
她想说的就这么简单。
再往下一层,为什么我们说巴特勒是一个后结构主义学者,是因为她把性别的观点给解构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类的活动方式是非常多元的,你仅仅借助一套与性别相关的概念,其实完全不足以概括。同样的,比如说两个人,他们重复同样被认为是生殖行为的动作,如果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义。
比如说,男女性交怀孕生孩子,对于包办婚姻的人和恋爱结婚的人来说,它同样是生殖行为,但它显然有不同的意义。通过这些例子想说的是,现有关于性和性别的话语系统,这些词都是大而化之的,都是对现实进行了某种剪裁和映射得出的东西。它并不足以显示出人类性活动的多元性。不管我们怎么细致的分类,我们没有办法穷尽人类的生理形态,也不能够穷尽人类进行的那些与性有关的活动,我们更不能一劳永逸的去规定到底哪些活动是跟性有关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巴特勒把性别这个概念给解构了。既然性别规范总是对无限差异的事实的约化、性别概念总要依赖这种规范,这些性别概念本身就不是稳固的。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当然即使你解构了这个概念,也并不能够让现实当中的性别规范就此消解。你不能够仅仅通过指出“性别规范本身是随着历史的变动而变动,不足以概括人类性别的差异,并不足以概括人类性活动的这种绝对的差异性”,就断言说这个性别规范可以不起作用、它所涵盖的那些压迫性的权力机制就不存在了。没有这么回事。
所以我说巴特勒她说的这个东西有启发,但是我们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去讨论她,就是这个意思。她说出了一些正确的废话,当然我觉得拿她来做一些启发性的讨论还是会有用。
< Q5 性,真的是亘古不变? >
比如说关于什么样的行为和性相关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一个动作,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它是否与性相关就完全不一样。《水浒传》里潘金莲和西门庆吃饭的时候,她把一只脚故意的放在西门庆面前。当时在他们的语境之下,一个女的把脚在男的面前露出来,那就是“勾引”。可是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之下,这个动作的性的含义是不是变少了?
说到“是否具有这样的含义”,我说的不仅仅是在文化体系符号体系之下,人们会怎么样解读这个动作。我更指的是当事人会对这个动作有什么样的反应。在那样的时代里边,如果一个女性她比较多的去谈论自己的身体的话,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就会被解读为与性有关的,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之下,(非常奇怪的是)男人会对这种行为产生性欲是广泛存在的,并且被认为是合理合法。
但是在今天如果女性穿的比较袒露的话,一个男的随便对一个穿得袒露的女性就产生性欲,就不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件很有出息的事。小说里潘金莲露出一只脚,西门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解读为“勾引”,但放在今天就不行。这并不是说男女的生理构造、生理机制,在这几百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你那么骚,就是在勾引我”这种想法还普遍存在,但是它遇到的反制力量也变强了。毋宁说,这是女权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女权运动最终让一些特定的行为动作“脱敏”,比如看着穿着不那么严实的人看得多了,性唤起的阈值也就高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女权运动让女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一定程度上自由选择穿什么、说什么的权利,以及反抗令人不舒服的性暗示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符号体系。
我们会发现,人的性唤起方式是和符号有关系的。符号体系改变了,人的性欲发展的方式似乎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连带着这些运作的方式全都发生了变化。在“性唤起”这个看似“纯粹生理”的机制与“性文化”这个“社会文化”层面的体系之间,好像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