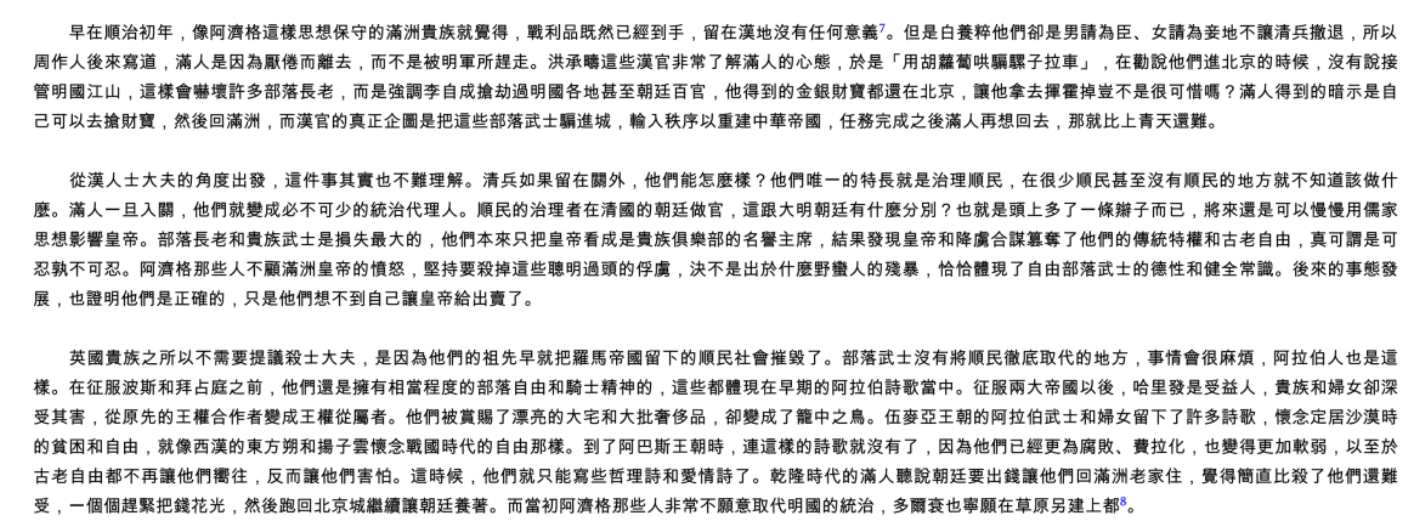asdf
njh

现代人已不耐于象征、暗示,动辄明开直讲,以致处处平民气,平民是不喜欢含蓄的。
华夏的土地已疲倦了,英伦三岛还处于中年期,虽然不如阿美利加之青壮,虽然时有一丝倦意显露,但底气仍然充沛,英国的土地未败,败的恐怕是人文,那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改名字的雅兴、学问,是否失传,我不敢说,但木心精擅此道。我亲见他为两三位朋友改过名字,当着面,笑吟吟地,片刻就想出来,多半根据对方的原名,换个字,便即好看好听——那改了的名字,此刻却想不起来了。
诱劝先生接受拍片的一刻,我的办法,就是不断逗他说笑话——这是他教我的。
得體而有趣。
我不愿描述这片刻。他头一次当我的面,失声大恸——那么多年,我只记得先生有过两三次微妙的哽咽:说起魏晋的嵇康与山巨源,说起托尔斯泰的出走,说起他夭折的小姐姐——有谁近半个世纪再没见过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吗?……转瞬,他展颜微笑,如小孩,一点不羞愧刚才的失态,又看照片,幽幽说起当年的情形:“大家都喜欢我……那是我第一次办个展呢……”之后他再看,再哭,顷刻收泪,无辜而失神地看我们,显然动着什么别的念头,然后仰面睡倒。
但我久已偏爱他的偏爱,看他怎样牢牢把守他的绝对标准,确切地说,他的标准,就是“绝对”,譬如:“美”……无分地域、国族、年代、主义,他对世界文学家各有所爱,可是他眷顾的画家(也许包括音乐家)少得可怜,只剩几个人、几幅画。他常说,待人宜宽厚,待艺术,必须势利(他狠狠说出:“必须势利”)。我渐渐赏阅他的“势利”:适巧相反,我仅偏爱几个文学家,却被太多画家吸引,喜欢各种毫不相干的画。
离校后的孙牧心并不关心前前后后的老同学,除了记忆,他刻意远避美术界。我曾问他:刘海粟怎样?“伊老滑头。”颜文樑怎样?“伊老实人。”徐悲鸿呢?他收了笑意,正色说:“误人子弟!”我喜欢听老辈说起更老的老辈,唯可诧异者,逾半个世纪,除了达·芬奇和塞尚,艺专的是非也一路跟着孙牧心。
我不以为浅薄,因为他是“上海人”。六七十年代上海弄堂的芸芸市井尚且以阿尔巴尼亚电影为蓝本,穷究高领毛衣的编织法,紧窄裤腿的接缝线,偷偷在家煮咖啡……何况孙牧心。现在想来,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的林风眠,纯真而可怜:年逾花甲,他竟请求从未出国的晚生孙牧心:“这样吧,你写一篇‘论纯抽象’。”而孙牧心居然“满口答允”……
近人他佩服齐白石。有次聊起国画,他想了想:“二十世纪嘛,总归还是齐白石顶好。”他也佩服傅抱石和潘天寿。有次聊起潘天寿大尺幅花卉,他说:“伊倒是笔力凶!”我问他今人的国画如何?“败相!”我问怎样的败相,他怫然怒道:“全错!”
木心画画(也许包括写作)力避讲求规模、投入劳作、耗时费工的类型。这是他懒么?他生就这路天性。事情不止于此:他对画种本身也不称心,他独钟林风眠,有道理的,林风眠先已在所谓国画和油画之间,寻了一条超然的路。
可能的理由是:出国须得卖画谋生。林风眠式的纸本彩墨,品相好看,木心抵美初年的年尾,纽约老藏家王季迁收了他的彩墨画,并请他住在曼哈顿林肯中心一带的高级寓所,后因王季迁要木心展示作画方式,未获应允,一九八三年夏,木心迁出林肯中心,移居皇后区“琼美卡”郡。
他心仪的西洋画家太少了,开不出前述访谈的那份名单。相较西洋文学与音乐,很久我才发现:木心并不果真迷恋西洋绘画。
他爱达·芬奇,是在蒙娜丽莎的肩后望见了“宋画”的渊深而雅驯,他那本唯一的画册,达·芬奇,并不翻看,是那份旧版画册的设计招他喜欢;他爱塞尚,并非意在塞尚苦心经营的结构,而是逸笔草草,还有,所谓“味道”。在纽约、伦敦,他逛美术馆差不多是在陪我,等我看完——再现的、逼真的、繁复的、叙述性的画,难以吸引他——远远扫视巴洛克厅堂的伟大经典,他从不入神地细看、久看,十八九世纪名画,更是一走而过。 “味道太咸了。”他带着轻微的嫌弃,轻轻说道,就像吃不惯西菜的那种表情。
他迷恋纸本。林风眠的影响源差不多全是纸本。纸本,不是西洋艺术的要项(甚至不是油画,而是雕刻,这一层,木心无保留赞叹古希腊)。纸、墨、毛笔,意味着中国的渊源——除了艺专时期,木心成年后即放弃油画。这一层他和鲁迅倒是相契(鲁迅说:原作都看不见,油画家等于摸“黑弄堂”)。有一回说起中国人弄油画,木心轻蔑地笑了,嗤道:“油画?做梦哩!”我大声同意他,他开心起来,顺口哄我:“侬倒还好,还可以……”我问为什么,他忽而收了调笑的语气,说:“侬老实呀。”
土,非中国。中国雅,雅之极也。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国最雅。 当然,他是在说先秦、魏晋、唐宋,那时还没有“中国”之说,但他用了这个词,亦且预先道断了英国人想要拍摄的主题。
巫鸿说到要点:木心创作,尽可能“抹杀”——在呈现中抹杀——他的画,他的写作,不彰显国族、不签署日期,转印画,则一律不签名。而“经典”的任何“模样”亦属他断然“抹杀”的部分:宋人元人的整套符号、图式、手法,在木心那里无法核对。他不谈中国画论(他擅律诗,玩《诗经演》,却也不谈中国的诗道),偶或拈来,必是语带戏谑。他在课中说道,都二十世纪啦,“还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那怎么行?”《西班牙三棵树》末辑有一首写在困顿年代的七律,其中有句:
陈丹青:他精致,我们粗糙?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试着不粗糙,就精致了吗——其实是贫薄、单一、匮乏、混乱。这时忽然出现木心,于是我们想到“粗糙”。“粗糙”,只是文字现象,或指粗陋的生活品质。但说木心“精致”,也没有说出他。我刚认识他时,他就说,做艺术家,做文人,要有点“草莽气”,不然不会有出息。很久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和官方文艺人来往,可是有草根朋友。要说粗糙,则他顶顶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陀氏写得“毛毛糙糙”,简直“望粗兴叹”!
陈丹青:不要把木心说成另外一个物种,好像他活在云端里——什么高人啊,超逸啊,博学高贵啊,遗世独立啊——还是我们的话语习惯,动辄大字眼,喜欢夸张,急于定性。把木心说成仙人,或对他冷漠,其实是同一种思维。 你要是听他话家常,谈小市民、乡下人,谈单位里弄堂里的鸡毛蒜皮,谈怎样做菜,穿衣,怎样调情,你会发现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健康的老头子。”
他和我们都用汉语写作。陈村说,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读读他。结果倒是许多八〇后九〇后读起来了,未必懂,但愿意读。追思会上好几位青年说,汉语好像就该是这样的。年轻人不一定讲得出道理,可是好的汉语,对的汉语,自有说服力。许多八〇后告诉我,他们不读五〇后六〇后写的任何东西。
陈丹青:对,不屑一顾。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傻乎乎跟人说木心,带去见他,后来发现好多人心里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一样。人会佩服他的才智,但心底里觉得这老头没成功,没名气,没被承认。他们看得起陈逸飞之类,看得起成功成名、有靠山有势力的人——他们那是看不起自己呀。
陈丹青:不。不要以为木心孤高隔世。他从不假定他的读者是一小撮高雅的人。他晚年有段笔记排列了他诚心诚意想象的读者,包括贩夫走卒,各色人等。 我有兴趣的是:为什么木心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七〇后八〇后?现在包括九〇后。
他常常是听着你说话,同时转自己的念头,立刻成句。陈丹青:希腊早先的传统很厉害,小孩长到一定时候,送出门,找个大人带他。古中国也这样,“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前提是有师傅。别以为师傅就是教授。从前弄堂里的乡下人都知道调弄小孩。木心最怀念带他长大的老佣人“海伯伯”,海伯伯给他讲故事,带他玩,木心讲起来活龙活现,到老还想念他,就像鲁迅想念闰土一样。
陈丹青:木心会从一句话,给你分析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引耶稣某句,说其实耶稣不喜欢这个人,但又不能点破,就顾左右而言他。还分析老子那句“民不畏死”,列出六七条解读——我们现在不会说话,也不会“听”,不会解,不会读。他说现在不解反讽了,说我出了本《退步集》,大家就说:看啊!他自己都承认退步了。
陈丹青:他不用这种词。教导的、励志的、格言式的话语,他不说。凡有目的性的话语和事情,他都不感兴趣,而且警惕。知行合一,你仍在指向一个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又指向道德规范。不,他没有的。他说:“你要在我书里找我的人生观,找不到的。”——这句话很难解,但很重要。我们半个世纪的写作和话语,就是一个表态的、定性的口号系统,木心不入这套话语的。
他顶喜欢的作家是高阳,专门推荐我看,杨乃武小白菜之类。我通宵读了,他好开心——木心喜欢高阳,是一个讯息。眼下爱木心的青年写起他,十之八九理解成如何唯美、超然,我读了不舒服,太花枝招展了,是在讲年轻人自己的文学幻觉。木心的趣味,那种质直的、带咸味的、南货店式的、老辣皮实的一面,年轻人没反应。
陈丹青:不是“矛盾性”,是复杂感。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感,他最感兴趣。
陈丹青:大部分时代是浅薄的,木心是在对不甘浅薄的人说话。你问他这些观念怎么会有,他在文学课中给你兜底翻出来。希腊、先秦,耶稣、莎士比亚、曹雪芹……有一组人物他翻来覆去说。这牵扯到他的另一个命题:天才。他总结哪个时代没有好文艺,一句说死:不出天才。你仔细想想,真是这样的。关于超人,他说超人早就有过,早就死了。超人和人类没关系的。他不相信进化论,他说尼采的超人还是进化论。尼采听到,肯定愣半天。
他还是那代人。他佩服周作人、胡兰成的才华,但私下不原谅他们失节。他给我看周作人的字,说,你看看这种字,所以失节呀。他是我爸爸妈妈那代人,忘不了。他谈日本文学,说是一九七几年恢复邦交,日本展览来上海,升太阳旗,老辈人一看就受不了,往事都想起来。这是很质朴的话。
陈丹青:智力没什么古代现代。木心在“文革”前就偷偷过现代生活,我们只是比他年纪轻,你以为到我们才“现代”啊?我跟他逛街,他看高级时装店橱窗,评头论足,说肩膀的斜线,对的,聪明的,又说裤子配这种驼色,真是懂。他进博物馆看前卫艺术,好多说法,可惜我忘记了。
你见过木心就知道,他对乡下孩子,对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完全就像跟我谈文学一样,跟他们谈。但他不是出于平等观,绝对不是——他曾说:平易近人,近什么人?——但他有句话很动人。他批判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他说,“他人即天堂”。天堂是个窄门,一个人都很难挤进去,两个人反倒挤进去了。
老派是一套规矩、规范。木心可以像鲁迅那代人写文言信。他好几次跟我讲,不要乱用文言。他给我解释“顿首”是什么意思,信尾不可以随便“顿首”,还要看尊卑亲疏等等,抬头,落款都有哪些讲究、套路,我是野蛮人,听了全忘了。
陈丹青:木心看不出身份、标志、年龄。你在文艺界老辈、晚辈、圈内、圈外,找不见这样的人。他日常谈话就是个上海老头,大半辈子隐在弄堂小单位,和市民职工打交道,随口市井语言。在纽约和知识分子结交,他就是绅士,老成,风趣,优雅。纽约的夏志清、王浩(数学哲学家)请他吃饭,惊讶地看着他。他和贝聿铭相谈,就是两个老派的、久在异国的江南老叶客,斯斯文文。他去哈佛办展,教授学生也为他的风度谈吐倾倒。这时你完全看不出他经历过什么。他和不同的人见面,作风语言都不同。晚生敬畏,唯因读到他的书,在书中,他隐去自己。